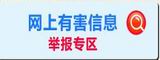对任何一个人而言,生与死都是世间事,而生是偶然的,死则是必然的。
我永远都忘不了近40年前我在一家基层医院当医生的遭遇。有两个病人,给我留下了特深的印象。
其中一位,姑且叫他A君,送进医院是因为得了视网膜炎。A君本人就是一名医生,户口在省城的他,却在那个包分配的年代,读完中专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镇医院,可见他内心是很失落的。高不成低不就的他一直不愿意在当地找女朋友,他甚至也不愿意结交身边的朋友,就那么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幻想有一天能通过婚姻或关系调回省城,直到他眼疾发作。
A君住进医院时,几乎分辨不出眼前的5元和10元。作为同行,A君当然知道他得的是一种可怕的眼底疾病,虽然不影响生命,但视力会天天下降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。
A君住在病区尽头的一个单间,每天接受一些保守治疗,而多数时候他就孤坐在床头。很少有人去看他,间或乡镇医院来人探视,鼓励他放下包袱,开朗一些,但他总是摇头。好几次,住院部的医生护士都开导他对治疗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,可他却说,他知道这种病的厉害,他对今生已不抱希望,说罢绝望地不断叹气……
A君病房的对面,住的是一位50多岁的肝腹水病人。他生病的起因是因为喝酒,酒喝多了伤了肝脏。因为病情危重,医生严禁他再近酒,可他偏偏在床头柜上放上一瓶酒,有事没事就打开来闻闻。劝解了多次,他才解释说,他当了10多年的铁道兵,常年累月战斗在野外,特别是打隧道感受了寒湿,常常要靠酒去驱散,一来二去成了瘾,转业后有了条件更是喝得起劲。现在住进医院当然是不敢喝了,可身体内的酒虫常常出来捣乱,所以闻一闻也是为了安抚酒虫在身体内的躁动。
这位铁道兵注定是不肯被病魔左右的,他在病区很有号召力,每周都要找两个下午组织病员读报,特别喜欢选读那些不愿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的文章。其他时间他喜欢互动,和病友交流治疗心得,回忆美好往事,憧憬康复后愿景。他自称是“肝大”学员,每次医生告诉他病情在恢复,肝硬化好转,肝大在缩小,他都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但我们是骗了他,他的病情是不可逆转的。有一天他从肝昏迷中醒来,看着身边的老婆孩子微笑着交待后事,他庆幸娶了贤惠的老婆,培养出了一个读大学的儿子,叮嘱他们今后别学他,要好好爱惜身体。
在我们集中精力抢救他的那个晚上,A君用床单结成绳索把自己吊在了吊扇钩上。这个并非医疗事故的“事故”,成了那晚所有值班医生护士挥之不去的内疚。大家想不通的是,一个连人民币都分辨不清的眼疾病人,又是如何站在摇摇晃晃的病床上,把绳索准确套进吊扇钩里的呢。
多年后我悟出了,当年的A君其实是在装病。生活的诸多不顺,亲情友情爱情的疏离,让这个来自大都市的青年慢慢抑郁了。可惜在那个年代,抑郁症对很多医生护士都还是个陌生的词汇,缺少心理疏导而简单归结于眼疾,让一心求死的他早早结束了而立之年的生命。
时光荏苒,社会总在不断进步。今天的我们,看待世间的生老病死更加坦然,生要好好活着,死要坦然面对。在时间的岁月中,我们来过,有一段美好的人生,有一段不枉的“今生”,也就无所谓“来世”几何了。

 四川法制网
四川法制网
 法治文化研究会
法治文化研究会



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
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